
图片来源:istanbulmodaakademisi
“包里有电脑、平板,照相机吗?”浦东机场安检人员机械地问。
“有电脑。”刘欣的回答无精打采,同样机械地从自己的Longchamp尼龙购物包里拿出一台11寸的Macbook Air笔记本电脑,放到了安检筐里——她显得非常不情愿,因为“以前去时装周,我哪用得着带电脑呀!?手机、iPad就足够了”——“这个Lonchamp的包,要不是为了放电脑,我已经好几年没用过了。”
临行前一天,担任某时装媒体资深时装编辑职位的刘欣在办公室耗了十几个小时,因为马上要奔赴即将开始的2017年春夏男装周,这次的目的地包括米兰和巴黎,她成功申请到超过30场新秀的邀请函。尽管已经去了6年的时装周,但她还是显得有些忐忑:一遍遍地核实所有邀请函的递送情况、和在米兰及巴黎负责接送机的司机再度确定时间、叮嘱助理完成各项稿件琐事、两个1万毫安时的充电宝从早晨开始便放在一边充电(“我还得拍现场发官微”),另外有个同事还在微信上托她带在巴黎带个Loewe的Puzzle包回来(“真他妈烦,不会从Ssense上买啊,买个包多占我行李箱啊!”)……从早晨8点到晚上10点,刘欣是倒数第二个离开办公室的。临走前,生活方式组正在加班同事跟她道别:“多好啊,真羡慕你们做时装的,又去巴黎”——刘欣呵呵一笑回之(“哪有你们天天出去住总统套、逛酒庄好!”)。
上海6月正值梅雨天,刘欣期盼一场大雨,心想下到机场停运最好。她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不愿意去时装周,因为从2014年开始,老板多布置了个任务:看完的新秀,要以最快时间写出一篇评论或报道,放在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上——人人都在讨论设计师如今的工作量过大而江郎才尽,但却没有人想到这些为公众号、数字内容KPI搞得焦头烂额的编辑、作者们有着同样的问题。
“真烦,现在的秀哪有什么可写的呀,尤其是男装,哪有什么变化啊!”刘欣发微信跟我说,她发的是语音,因为“不想打字”。
“那你就随便写写呗,灵感啊、廓形啊什么的,Vogue网站上出了秀评跟着扒一扒不就完了。还有什么男女装合并、时装业面临革新之类的。”
“我们老大说要有观点,不能说帅翻了美爆了。有个屁观点,客户衣服再难看,我也不能说,只能捡那些不投钱,在中国没店的说。跑了一天回来累都累死了,还得写那破微信稿子。我有次写到半夜妆都花了,屏幕关上时我一看我跟刚被蹂躏完一样。”
“你说我要不要买一台新出的Macbook呀,就那个不能插U盘的”,刘欣的话题突然逆转。
“干啥用啊?你不是去年才买了新电脑嘛!”
“写秀评写稿子呀!那个比较好看,我喜欢黑色的。”

在微信公众号还没流行以前,杂志时装编辑出席时装周的任务表上,附加的工作是在巴黎、米兰拍几组时装片,但随着预算的减少和同类型拍摄的增多,如今拍片不再是重点,而变成了微信推送内容。
单一品牌时装秀评论、报道除了在中国时装杂志初期发展时有过涉及,在后期却被抛弃,因为月刊的出版频率完全达不到实时更新的要求,另外多数刊物会认为此类稿件操作难度较低,只能当做集锦杂盘,比如选择在时装周结束后进行一轮以图为主、文字为辅的潮流点报道(充斥着“印花当道”、“色彩迷宫”,“奢华军装”之类的陈词滥调),而那些想要获取“深度”美名的,则会用文化、艺术等领域的概念包装,效果虽比第一种略有姿态,但也难逃“看图不看字,翻翻就过去了”的命运。
社交媒体流行后情况大有转变,除了微博、微信上的KOL们不厌其烦地跟着Vogue Runway更新,传统时装杂志的新媒体平台也不甘落后——“这场秀我们微信平台全网首发,各位再接再厉!”某女性时尚类刊物负责人在编辑部微信群里说到,彼时已经是北京时间深夜1点多,但她得到了五六个象征“胜利”、“加油”的表情回复——其实编辑团队并没有奔赴时装周,而该刊物的内容架构里,时装也向来不是核心,但在随大流的心态和每日更新的领导要求下,平媒还是靠着新媒体找到了久违的高潮。
目前担任《纽约时报》时装总监暨首席时装评论人的Vanessa Friedman曾表示她会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类时装秀,重点在于奔走的过程中,她能通过观察人群间的气息,从而引发她从全局思考的观点。对此,Business of Fashion中文版的执行编辑主管Queennie Yang亦持有相似的观点:“当你身处时装周,你可以观察周边人的反应和态度,这对时装周报道很重要。”


Vogue.com和Dazeddigital.com在刚刚过去的2017春夏男装周中所完成的”偏门“报道
但刘欣对于目前男装周的反应是“萧条”,她表示今年的男装周尤甚:“以前我也觉得你得真在现场才能写评论,但现在看来也不是必须的了。没什么特别令人值得注意的,有的秀场很热闹,但衣服一般般甚至挺差的;有的看上去挺好看,但仅此而已。另外就是一群穿着那种很街头的衣服的小孩越来越多了,但我觉得除了抓人眼球没什么别的,很难看,这种品位我是不懂”——那如果时装秀本身泛泛可陈,又如何完成一篇篇的秀场评论、报道呢?以Vogue Runway(前身为STYLE.com)为首的一众欧美时装媒体做出了样本,以“N件关于XXX新秀你需要知道的事”、“本季最值得聆听的X首秀场歌单”等剑走偏锋的模式完成报道,这有点像娱乐报道的做法,但对于记录一场秀而言仍不为过,对于需要撰写时装评论的人来说,这些偏门别类的信息也有助于他们的描述(“写写音乐、布景,300字就出来了”);国内媒体在经历了被指责用词夸张毫无水平(”太美了”、“都想要”……)以及过度网络语言口水化后,也逐步开始使用第一人称描述的日记体、或者是更讨喜的“明星带你看时装周”模式。《GQ智族》中国版从去年开始以短视频、编辑出镜、迷你采访时装周幕后工作人员甚至路人的做法获得了不少好评,但面对愈加喜新厌旧的受众而言,这种编辑手法的可持续性有待商榷。
Queennie Yang和目前已经辍笔的资深时装人林剑都表示他们已经丧失了对“正统”时装评论的兴趣。“首先现在的时装也没什么太大意思,曾经好的评论对买手啊都有参考价值,但现在这东西已然显得太主观了,我更感兴趣新闻性强的内容,比如Suzy Menkes写得没什么观点,但她几十年做下来,是好几个时代的记录者,这可能对今后的从业者有个史记式的作用。”林剑说。
但看起来杂志腔调十足的“传统“时装评论仍旧对衡量一个媒体从业者水平有一定作用,这点在那些想要挤进这个圈子的人来说尤甚。24岁的王卫,大学主修社会学,但志向却是成为有话语权的时装评论人。从大三开始,他开设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撰写在内行看来很水的时装评论,并在微博上和那些有认证信息的时装杂志编辑死磨硬泡,终于以300元千字的过时稿费价格为某周刊写了几次潮流总结的稿子。虽然稿费一直未付,但他还是很自豪地把自己的Linkedin状态从一纸空白更新为“时装作者”,可这仍旧与目标差距甚远:“我不喜欢Gogoboi那样娱乐化的博主,我想像Tim Blanks,或者像你写过的Nirokita那样。”为此,王卫准备去国外研读有关时装写作的课程:“我去年在Linkedin上收到一个Tim Blanks办的时装写作培训班的私信,也不知道真假,但我想去,不过后来我想还是要读个有文凭的回来,比如去圣马丁。”
“年轻人,需要表达,需要发声,拿个话语权嘛,然后可能再看看有什么进一步发展的途径。”林剑对于一拨主攻传统时装评论的青春少艾们的看法非常包容。“时装设计也好、评论、写作也好,我不觉得是能在学校学出来的,至多是换个人生经历。现在是个人都能说自己是评论家,你凭什么写,就凭喜欢!?凭看了几张图或者参加过几次fashion weeks!?我做记者那几年发现写几次就词穷了,直到我后来做了retail(零售),不了解这个你没办法从整体去说。评论,主观看法是一定要有的,但如果缺乏整个行业链的认识,只能是自说自话,没什么分量。”曾有过短暂时装媒体经历、现服务奢侈品零售行业十余年的Ken Tsui的态度则更为激进些。
名声和地位的确影响着时装评论人的话语分量,对此曾服务《周末画报》、为多家媒体撰稿的Pooky Lee也持同样的想法:“我更看重评论人的从业背景和经历”。不过这仅限于业内人士而言,对于普罗大众,则显得没那么重要:“很容易嘛,就写得晦涩点难懂点,玩文字游戏嘛!再在朋友圈、微博上发点Vestoj,Garmento这类小众杂志的内页。我看了不少书呢最近,哲学的、服装史的,有很多话用在稿子里,显得很有分量。我这样写了几篇了,粉丝数都涨了上百个。”我惊讶王卫毫无掩饰的坦诚,却丝毫不惊讶他能总结出得到这样的套路,衡量一个作家、艺术家,敏感与否甚至超过了后天的勤奋,王卫很敏感,但专于揣测人心。“就算转发的人也不见得真看过他们转的东西,他就是觉得转了会显得很酷。”Queennie Yang说。
时装评论本质上和其他评论作品如出一辙,不知柴米油盐贵,难做时装评论人,读书或许能补充常识,但换到真正跃然纸上的内容,倘若作者的个人生活、经历、思维过于局限难以延伸不够敏感,其作品注定只能成为一场文字游戏。这点,知名时装评论人Charlie Porter、Alexander Fury等都表示过时装记者和撰稿人不应该太过束缚自己所涉及的领域。此外,抛开学识、从业背景等因素,理想地说,一个优秀的时装评论人、编辑应当有不输于当代设计师的设计思维,不然极为容易盲从。
同时,时装评论、报道向来被诟以“充斥着华丽辞藻、有悖评论二字的变相赞美”的恶名,Vestoj曾以此为题炮轰Alexander Fury撰写的关于Alessandro Michele及Demna Gvasalia是何等“革命”的文章自圆自说左右逢源,以及Dazed Media集团创始人Jefferson Hack是如何披着“独立”外衣为品牌做软文的;A.P.C创始人Jean Touitou也对时装媒体的职业操守有所抱怨(“Dolce & Gabbana漏税的事儿搞成那样,没有一本时装杂志敢说,因为他们投广告”)——“没办法,这就是游戏规则,在国内估计看不到什么说实话的东西了,我现在看到微信上关于时装周的内容就恶心。”刘欣说,此时她正在巴黎,为报道新秀的稿子想词儿。“我们不太关心时装评论这回事儿,杂志肯定不敢,除非名气太大的人说了我们不好,我们会介入,但单个人的名声再大也没品牌大,所以这还是狼和羊的关系,再说国内也不存在像什么Cathy Horyn(曾因对Saint Laurent、Girogio Armani等品牌的负面报道而被封杀)那样的人,就算以后有了,照样能搞定”,某奢侈品公关经理解释到,此外他出于好意,还不忘提醒我:“你现在给界面做的时装周稿子,可要注意言辞啊,别在上升期时候遭人封杀。”
“实话”无非就是丑或美,但这不是评定一个系列最至关重要的因素,因为审美因人而异带有强烈的主观因素。“现在,时装评论可能在朋友圈,Instagram里,衣服好看不看大家一目了然众说纷纭,这个品牌就控制不了了,从一场秀发展到行业评论的东西,字太多的没人会看。”但Ken Tsui的说法还不能满足中国的时装媒体,就算没人看,也要有字,哪怕是充当版面的陪衬:“不放点字儿上去,好像不叫稿子吧!?”即便被搞得蓬头垢面,刘欣却坚守“要有字儿”的做法——秀场必须继续,所谓的评论和报道也只能接踵而来,管它是糟粕还是碧玺。
“但这也挺矛盾的,英国脱欧那天我很不开心,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多年。我觉得时装界也一样,如果全靠民意,总是迎合大众喜好,这个行业会做不下去,但右派的人又被看作老古董,时装界的人也从来不爱接受批评。主要还是一群徘徊在中间的人,东倒西歪,没什么有用的见解,更谈不上立场。”Ken Tsui补充到。
“咱们上学写作文时候就都是滥竽充数,得琢磨老师的喜好,现在也一样,琢磨老板和客户的喜好,脑子早就成僵尸了。”刘欣在巴黎的行程即将结束了,她说想改行,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再让她觉得有意义了。
“我准备换助理了,找个会写东西的,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。给稿费,100块一篇”,她在微信里和我说。
“要写啥啊?”
“写秀评、写微信呀!”
看来,她不用买新款的Macbook了。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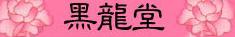


 粤公网安备44030702000122号
粤公网安备44030702000122号